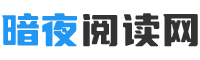由知名作家“东北马哥”创作,《梨园哑师》的主要角色为【苏晚棠顾昭赵雪儿】,属于言情小说,情节紧张刺激,本站无广告干扰,欢迎阅读!本书共计29174字,梨园哑师第1章,更新日期为2025-09-16 18:08:05。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已完结。小说详情介绍:苏晚棠的身影,被烛火投射在幕布上,纤细,又孤单。她没有演,只是静静地站着。台下的观众开始骚动,交头接耳。前排那中年人手里的核桃也停了。就在这时,沈清音的琵琶响了。只有一个音,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清冷,悠长,带着回音。幕布上,苏晚棠的身影动了。她举起手,一个皮影人出现在幕布中央。正是那个眉目悲悯的新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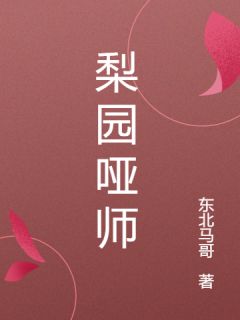
《梨园哑师》免费试读 梨园哑师第1章
暴雨砸在青石板上,溅起浑浊的水花。
苏晚棠蹲在破庙台阶下,指尖沾了沾雨水,将打湿的皮影线理顺。
她面前支着块褪色的蓝布幕,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后面歪歪扭扭的竹架——这是她用捡来的竹片和破布搭了三天的戏台。
"要演了!"缩在墙根的小乞丐吸着鼻涕喊了一嗓子。
七八个裹着破棉絮的流浪汉立刻围过来,雨水顺着他们乱蓬蓬的头发往下淌,却没一个人挪动半步。
苏晚棠深吸一口气,喉结动了动。
她发不出声音,可指尖的皮影会说话。
窦娥的牛皮影被她托在掌心,朱红的裙裾还沾着昨夜熬胶的痕迹。
她手腕轻抖,皮影"唰"地跃上幕布——是法场的戏。
雨幕里,窦娥的影子在风中摇晃。
苏晚棠的拇指抵着皮影后心,食指勾住右臂的丝线,每寸动作都跟着记忆里的说书人腔调走。
当演到窦娥骂天"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时,她的指甲几乎掐进掌心,眼尾泛红,喉间发出极轻的呜咽。
最边上的粗壮大汉突然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这...这窦娥的冤,咋比我当年被老财打断腿还疼?"
小乞丐把啃了一半的炊饼攥碎在手里,抽抽搭搭地说:"姐姐的皮影在哭,我这儿也在哭。"
蓝布幕被雨打湿,透出苏晚棠的影子。
她弓着背,雨水顺着发梢滴在青布衫上,洇出深色的水痕,可指尖的动作始终稳当——这出《窦娥冤》她看茶馆的说书人讲过七遍,在破庙里对着月光练了十四夜。
每个甩袖的弧度,每个抖肩的频率,都刻在她脑子里,比刻在木头上还深。
直到幕布上的窦娥缓缓倒下去,苏晚棠才松了松发酸的手腕。
流浪汉们沉默了片刻,突然有人用破碗敲出清脆的响声——那是他们能给出的最热烈的喝彩。
"拿去吧。"粗壮大汉摸出个半块的炊饼,塞进她怀里,"比城里戏楼子唱得真。"
苏晚棠低头笑了笑,指尖轻轻碰了碰那半块炊饼。
她把所有"赏钱"都收进竹筐时,雨已经停了。
青灰色的云被风撕开条缝,漏下一缕晨光,照在她腰间的铜铃铛上——那是师父临终前给她的,说"哑人演活戏,铃铛替你唱"。
第二日清晨,苏晚棠在街头支起幕布时,竹筐里还剩两个冷掉的炊饼。
她正低头调整皮影的金线,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冷笑。
"玉茗楼选角,要看真本事。"
沙哑的男声让她脊背一僵。
她转头,看见个穿灰布长衫的老者站在三步外,背着手,下摆沾着泥点——是玉茗楼的账房李伯。
上个月她在茶棚外听过他说话,玉茗楼要在江南采选新角儿的消息,还是他敲着算盘说的。
"哑巴演戏?"李伯扫了眼她的皮影,眉头皱成个结,"不过是滑稽把式。"他甩了甩袖子,转身要走,"玉茗楼要的是能唱能念的角儿,不是靠手底下抖机灵的。"
苏晚棠的指甲掐进掌心。
她想起昨夜流浪汉眼里的光,想起师父临终前摸她手背说"棠儿的戏有魂",喉间泛起酸涩。
"哟,这不是当年被陈三娘赶出去的哑丫头么?"
另道声音像根细针,扎进她耳朵里。
苏晚棠抬头,看见月白缎子外衫的柳文远站在人群前,折扇"啪"地敲在掌心——他是陈三娘戏班的头牌小生,当年正是他跟着喊"哑巴比不得饭吃,还占着戏班口粮"。
"陈三娘好心收留你五年,你倒好,连句完整的戏词都学不会。"柳文远斜睨着她的皮影,"现在靠耍皮影混饭?
也配说自己是梨园的人?"
围观的人哄笑起来。
有个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摸着胡子点头:"到底是哑的,再怎么摆弄皮影,能比得上文远公子的《牡丹亭》?"
"就是,上回文远公子唱《惊梦》,连张员外家的**都抛了金镯子。"
苏晚棠的手指紧紧攥住皮影线。
窦娥的皮影被她捏得变了形,可她忽然想起师父说过的话:"哑人演戏,要让眼睛替嘴说,让影子替人活。"
她深吸一口气,突然抖开皮影线。
还是《窦娥冤》的法场戏。
这一回,她没等任何鼓点——昨夜茶馆里的老鼓手敲的节奏,早就刻在她骨头里。
腕子轻抖,窦娥的皮影扬起头,红色盖头被她用小拇指挑得飞起,正应着"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的唱词。
围观的人渐渐静了。
柳文远的折扇停在半空,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他分明记得,昨夜在醉仙楼听老鼓手说,自己新谱的《窦娥冤》鼓点改了三回,可眼前这哑女的皮影动作,竟和他刚定的节奏分毫不差。
"好!"
苍老的喝声炸响。
人群里挤进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的旱烟杆敲得青石板"咚咚"响,"这哑女的皮影有魂!
你们只看她不能开口,可你们看——"他指着幕布上颤抖的窦娥,"窦娥临刑前那股子恨,那股子冤,比戏楼里那些扯着嗓子喊的,真上十倍!"
苏晚棠的眼角湿了。
她望着老头,喉咙动了动,用口型说了句"谢谢"。
老头冲她挤挤眼,从怀里摸出枚铜钱,"当"地扔进她的竹筐:"这钱,买你一场真戏。"
人群里的议论变了。
小媳妇抹着眼泪说:"我方才真觉得窦娥站在面前。"卖糖葫芦的小贩挠着头笑:"比我闺女看的话本还揪心。"
柳文远的脸涨得通红,折扇"咔"地折起来,转身就走,月白外衫下摆扫起一阵风。
李伯没走,他盯着苏晚棠的皮影看了许久,喉咙动了动,终究还是没说话,背着手挤进人群里。
苏晚棠蹲在地上收皮影,指尖抚过窦娥的脸。
竹筐里的铜钱叮当作响,混着那半块炊饼的香气。
她抬头望向街尾的方向——那里挂着块"玉茗楼"的烫金招牌,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巷口突然传来马蹄声。
"让让!让让!"
苏晚棠抬头,看见两匹青骢马踏碎晨雾而来。
为首的年轻人穿着玄色锦袍,腰间玉佩随着马速轻晃,他勒住缰绳时,目光恰好扫过她的皮影幕布。
"什么人在喝彩?"他问身边的老仆。
老仆伸长脖子看了眼,笑:"许是哪个街头卖艺的。"
年轻人没说话,目光却落在苏晚棠身上。
她正低头整理皮影,发间的铜铃铛被风掀起,"叮"地响了一声——像极了戏台上那声绕梁的尾音。
顾昭的青骢马在巷口缓下脚步时,耳畔的喝彩声正像被投入沸水的茶叶,在晨雾里咕嘟咕嘟翻涌。
他原是随父亲南下收一批苏绣,途经这条青石巷不过顺路,却被这异于寻常的热闹绊住了马蹄。
"去看看。"他对身边老仆陈福抬了抬下颌。
玄色锦袍下摆扫过马镫,落地时带起一片碎金般的晨光——这是京城玉茗楼少东家惯有的从容,连下马的动作都像戏文里的武生,利落得挑不出半分错处。
穿过攒动的人头时,陈福直咂嘴:"不过是街头卖艺的,您这是..."话音未落便被眼前景象堵了回去。
一方褪色蓝布支成的皮影幕前,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正垂首摆弄竹棍。
她的手指极细,骨节处泛着常年握竹棍的淡青,可那双手落在皮影上时,倒像戏楼里最金贵的琴师抚过瑶琴——窦娥的皮影被她挑着,红盖头在风里打了个旋儿,正应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气性。
顾昭的呼吸顿了顿。
他见过太多戏子的窦娥:有的扯着嗓子嚎得脸红脖子粗,有的挤眉弄眼装委屈,可眼前这皮影里的窦娥,偏生在那片晃动的影子里立出了脊梁骨——她跪得直,仰头时眼尾挑得狠,连被风吹得摇晃的盖头,都像是要掀了这混沌的天。
"好!"白胡子老头的旱烟杆敲得石板响,"这哑女的皮影有魂!"
顾昭的目光这才落在姑娘脸上。
她生得不算极美,可那双眼睛亮得惊人,眼尾微微上挑,此刻正泛着水光——听见喝彩时,她喉咙动了动,用口型说了句"谢谢",像是怕惊碎了这来之不易的掌声。
"她是哑的?"顾昭低声问陈福。
陈福眯眼瞧了会儿,点头:"方才那老头喊了,说是哑女。
您看她竹筐边的木牌,写着'哑影'二字呢。"
顾昭这才注意到,姑娘脚边立着块半旧木牌,墨字被雨水浸得有些模糊,却能辨出"哑影苏"三个小字。
他往前半步,正见她低头收皮影,发间铜铃被风掀起,"叮"地一声——清冽得像《长生殿》里杨贵妃摔碎的玉笛,余音绕在人胸口,半天散不去。
"走了走了!"
月白外衫的影子从顾昭身侧擦过。
柳文远攥着折扇的指节发白,方才在醉仙楼还夸口"江南第一小生"的傲气全碎在这巷子里。
他原是想来看这哑女出丑的——谁不知道街头卖艺的最会糊弄人?
可她演的窦娥,竟比他在戏楼里练了三个月的《斩窦娥》还像那么回事。
"顾公子?"柳文远猛地顿住脚步。
他认出了顾昭腰间的玉牌——那是京城玉茗楼的标志,连皇帝都夸过"玉茗楼的戏,能唱到人心坎里"。
顾昭抬眼:"柳公子这是?"
柳文远的折扇"唰"地展开,掩住半张紧绷的脸:"不过是路过瞧热闹。
顾公子莫不是对这哑女的把戏感兴趣?"他嗤笑一声,"她连句唱词都说不全,能有什么真本事?
玉茗楼要收这样的人,传出去可要被同行笑掉大牙。"
顾昭没接话。
他望着柳文远泛红的耳尖,想起方才皮影幕上窦娥甩袖的弧度——那分明是按昨夜醉仙楼新改的鼓点来的。
柳文远新谱的鼓点改了三回,连陈福都听他在马车上抱怨"那老鼓手太倔",可这哑女的皮影,竟比柳文远自己记的还准。
"柳公子的《窦娥冤》,倒是教她学了个十足。"顾昭似笑非笑。
柳文远的脸腾地红了,折扇"咔"地合上,匆匆作了个揖便快步离开。
青石板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倒像是被人抽了脊梁的戏子,连台步都乱了。
陈福凑过来:"您真要为个哑女多留几日?
玉茗楼那边还等着您带苏绣回去呢。"
顾昭望着姑娘收完皮影,蹲在地上拾铜钱的模样。
她的竹筐里除了铜钱,还有半块炊饼,沾着星星点点的芝麻,许是今早没来得及吃的早饭。"去查查她的底。"他说,"陈三娘带大的那个哑女,我倒要看看,她到底能把皮影演成什么样。"
陈福领命而去时,顾昭摸出块碎银,悄悄扔进了姑娘的竹筐。
铜钱堆里突然多出块银锭,她猛地抬头,正撞进他的目光里。
他冲她微微颔首,转身时听见她喉咙里溢出一声含混的"嗯"——像春夜融雪的溪涧,带着说不出的清亮。
这一留,便是三日。
顾昭躲在茶棚二楼,看她演《牡丹亭》的杜丽娘。
皮影的裙裾被她挑得像沾了晨露的花瓣,"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唱词虽从旁人嘴里念出,可那皮影的眼波流转,比戏楼里唱得最甜的花旦还多三分魂。
他又去问了卖糖葫芦的小贩,问了洗衣的小媳妇,问了总在巷口下棋的老头——人人都说这哑女的皮影"能把人看哭",说她"记戏文比先生背书还快",说她"半夜还在灯下补皮影,灯油钱都是省出来的"。
第三夜,顾昭站在破落的瓦屋前。
窗纸透着昏黄的光,映出姑娘的影子——她正坐在桌前,拿细针修补窦娥皮影的水袖,针脚细得像游丝,连断了的丝线都要重新编过。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
苏晚棠猛地回头,手里的针"当"地掉在地上。
眼前站着个穿玄色锦袍的青年,腰间玉佩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的目光像戏台上方的灯笼,亮得让她有些晃眼。
"我是顾昭,京城玉茗楼的少东家。"他的声音像浸了温酒的玉,清冽里带着暖意,"我想请你去京城。"
苏晚棠的手指攥紧了皮影的竹棍。
她望着顾昭身后的月光,又望着他眼里的真诚,喉咙动了动,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
夜风掀起她的衣角,发间铜铃轻响,像是替她应了半声。
顾昭没有催促。
他望着她泛红的眼尾,想起三日前她收皮影时,竹筐里那半块炊饼——想起她说"谢谢"时的口型,想起她演窦娥时眼里的那股子狠劲。
"玉茗楼的戏台,该有能唱到人心坎里的戏。"他轻声说,"而你的戏,该被更多人看见。"
苏晚棠怔在原地,久久未语。
她看着眼前陌生却真诚的顾昭,喉结动了动,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皮影的水袖。
窗外的月光漫进来,落在她发间的铜铃上,又落在顾昭腰间的玉牌上——两块玉,一块铃,在夜色里静静发着光,像两盏未点的灯,等着被戏里的火,烧得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