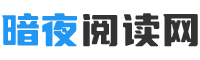主角分别是【许知言霍屿】的言情小说《每天醒来,都忘记昨天发生了什么》,由知名作家“无端锦瑟觅”倾力创作,讲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本站TXT全本,期待您的阅读!本书共计30919字,每天醒来,都忘记昨天发生了什么第3章,更新日期为2025-11-06 15:24:57。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连载中。小说详情介绍:”一个听起来很职业、略带焦急的女声传来。“我是。您是哪位?”“许先生您好,我是《艺术鉴赏》杂志的编辑,我姓王。我们之前约好今天上午十点,在‘流金岁月’会所的‘听雨阁’茶室,做一个关于古代丝织品,特别是唐代蹙金绣工艺修复的专访,您还记得吗?我们这边已经都准备好了,摄影师和灯光师也就位了,您看大概什么时...

《每天醒来,都忘记昨天发生了什么》免费试读 每天醒来,都忘记昨天发生了什么第3章
询问室的灯光冷白得刺眼,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将许知言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蒸发殆尽。衬衫纤维的发现,像一记精准而沉重的闷拳,不仅砸在他紧绷的神经上,更彻底撼动了他赖以生存的、用笔记和录音构筑起来的秩序之壳。那感觉,如同一个虔诚的信徒,突然发现自己笃信的经文竟是伪作。
“我……我需要看看我的笔记和录音。”许知言的声音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微颤,那是一种源于根基动摇的恐慌,“我需要知道‘昨天’……那个对我而言一片空白的‘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霍屿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用那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持续地、冷静地审视着眼前这个男人。许知言此刻的反应——那种并非表演出来的茫然,那种深陷迷雾找不到方向的无力感,以及那种对自身记忆近乎本能的不确信——都细致地落在他眼中。这种状态,极难伪装。
沉默在冰冷的空气中蔓延了几秒,霍屿才几不可察地颔首。“可以。”他朝负责记录的年轻警员示意了一下。警员起身,将之前暂时保管的许知言的个人物品——那本质感厚重的皮质笔记本和那支黑色录音笔——递还到了许知言手中。
许知言几乎是急切地,甚至带着点抢夺意味地接了过来,冰凉的皮质封面和金属笔身让他因紧张而发热的指尖稍微冷静了些。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首先翻开了那本记录着他“昨日”的笔记。
他的目光迅速而专注地扫过10月25日那一页。上面是他熟悉的、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字迹:
“上午:修复明代青花瓷瓶(编号:MC-2023-087),接底工序完成百分之七十,釉色匹配度良好。
下午:于书房查阅三年前‘8·15’美术馆失窃案公开卷宗(复制件),重点关注失窃文物‘夔龙纹青铜罍’流向推测,无实质性新发现。
晚间:自行烹制番茄鸡蛋面(食材消耗:番茄两颗,鸡蛋一枚,挂面适量)。
备注:左肩旧伤(源于三年前事故)于晚间九时左右出现轻微酸胀痛感,未用药。
就寝时间:约二十三时三十分。”
记录简洁、客观,逻辑清晰,一如既往。没有提到任何计划外的外出,没有提到那个叫赵永的收藏家,更没有一丝一毫与血腥命案相关的痕迹。他甚至下意识地用指尖摩挲了一下那页纸的边缘和书写墨迹,触感平滑,墨迹干透,没有任何刮擦、涂抹或后续添加的迹象。
他合上笔记,动作略显沉重,然后拿起了那支录音笔。找到昨天晚上临睡前的录音段落,再次按下播放键。他自己的声音在过分安静的询问室里响起,温和,带着一丝终日与寂静相伴而产生的疲惫感,语调平铺直叙:
“知言,晚上好。现在是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十一点。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说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而你又成功地……或者说,不幸地,忘记了今天的一切。”
(轻微的叹息声)
“今天的工作还算顺利,那个明代的瓶子底足接得不错。下午又看了一遍三年前的卷宗,还是没什么头绪。霍屿警官那边似乎又有动静,他今天调阅了你的医疗记录和近期的出行记录。我知道你一直想弄清楚真相,但……面对他,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个人,像一把出了鞘的刀,太锋利了。”
(停顿,似乎是喝了口水)
“明天上午九点要去美术馆,那批追索回来的文物需要你做初步评估,资料已经准备好了。记得吃早餐,牛奶在冰箱第二层,吐司在储物柜左边,果酱快没了,记得补货……就这样吧,晚安,祝明天的你……好运。”
录音结束。内容与笔记完全吻合,语气、情绪都符合他对自己一贯的认知。平静,略显沉闷,带着对霍屿的警惕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但绝无任何与谋杀相关的紧张或异常。
笔记和录音,这两个他倾注了全部信任、用以对抗虚无的“外部记忆”,共同为他构建了一个清晰、平静、按部就班的“昨天”。它们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他:你昨晚安分守己地待在家里,修复文物,查阅资料,吃一碗简单的面条,与那栋奢华却充满死亡气息的别墅,与那个名叫赵永的陌生死者,没有任何时空交集。
那么,现场那该死的、与他身上这件崭新衬衫材质完全一致的棉线纤维,究竟从何而来?难道它能凭空产生,穿越时空,附着在一个它本不该出现的地方?
许知言抬起头,目光越过冰冷的桌面,再次投向霍屿。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真实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困惑,以及一种濒临绝望的坦诚:“霍警官,我的所有记录都显示,我昨天没有离开过家,更没有接触过任何可能产生那种纤维的外部环境。我……我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这不合逻辑。”
霍屿身体向后,靠进坚硬的椅背里,双手交叉随意地放在身前。这个姿势让他看起来稍微放松了一些,但那双眼睛里的审视光芒却丝毫未减。“许先生,”他缓缓开口,声音平稳得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办案,讲究的是证据链,是客观存在的物证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一起与三年前未解悬案相关的命案发生了;一件疑似与该悬案核心文物有关的诡异物品,离奇出现在你即将工作的、相对私密的空间里;而你的个人物品纤维,又明确无误地留在了命案现场的核心区域。”
他微微前倾,目光更具压迫感:“这一系列的客观证据,环环相扣,都指向了你。相比之下,你单方面的、基于……某种特殊生理状况的个人记录,其证明力,在法律层面和侦查逻辑上,都显得非常有限。”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给许知言消化这些话的时间,也像是在斟酌更准确的措辞:“我理解你的情况特殊,这种……记忆上的障碍,并非你主观意愿。但法律面前,讲究的是公平和平等。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得起反复推敲、能够被第三方验证的合理解释。而不是一个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我不记得’。”
许知言沉默了,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知道霍屿说得冷酷,但却在理。在指向明确的物证面前,他这具会呼吸、会行走,却丢失了“过去”的躯壳,以及他那套赖以维系认知的脆弱系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的“遗忘”,在这种情境下,更像是一种精心计算过的、完美的托词。
“或许……”许知言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喉咙干涩发紧,一个让他自己都脊背发凉的念头不受控制地浮出水面,“有人……能够接触到我的物品,在我的笔记上做了手脚?或者,在我完全不知情、也无法记忆的情况下,有人拿走了我的衬衫,穿去了某个地方,再放回来?”
这个猜测说出口的瞬间,连他自己都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这三年多来,严格遵循、视若救命稻草的秩序和记录,从始至终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意味着他所谓的“安全屋”,其实四处漏风,早已被无形的黑手渗透?那他还能依靠什么来确认“许知言”这个存在的真实性与连续性?
霍屿的目光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许知言提出的这个可能性,他并非没有考虑过。三年前的“8·15”案,牵扯深广,背景错综复杂,像一团理不清的迷雾。师父张海峰的殉职,至今仍有许多疑点悬而未决。如果有人想利用许知言这个记忆缺失的“活证人”做文章,将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并非没有动机和可能。
“这是一种推测方向。”霍屿没有否认,语气依旧保持着刑警的审慎,“在侦查工作中,任何合理的可能性都需要被纳入考量。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重新变得锐利,“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在找到支持你这一说法的确凿证据之前,基于现有的物证链,你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调查的对象,嫌疑无法排除。”
他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示意这次问询暂时告一段落。“许先生,今天的笔录就先到这里。在案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者你的嫌疑没有被彻底澄清之前,请你保持通讯设备二十四小时畅通,暂时不要离开海城市区,我们可能随时需要你配合进一步的调查。”
这是程序上的要求,也是变相的监控和限制离境。许知言木然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像是一个被抽走了部分灵魂的木偶,动作有些迟缓地站起身。
就在他走到询问室门口,手即将触碰到门把手的瞬间,霍屿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不高,却清晰地钻入他的耳膜。
“许先生。”
许知言脚步一顿,缓缓回过头。
霍屿站在桌边,没有看他,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份刚做完的笔录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纸张边缘。他的侧脸线条在冷光下显得格外硬朗,但语气却似乎比之前少了几分公事公办的冰冷,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回去之后,找个安静的时候,抛开固有的认知,再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那些‘记录’。也许……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太过于习惯,反而被忽略了。”
这句话,不像是一个严厉的审讯者发出的最终通牒,更像是一种基于某种直觉的、隐晦的提醒。甚至带着一点……同为追寻真相者的共鸣?
许知言微微一怔,心底掠过一丝极其微弱的、难以捕捉的暖流,随即又被更大的迷雾所淹没。他低声道:“谢谢。”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
走出市公安局那栋庄严肃穆的大楼,秋日午后的阳光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温暖,明晃晃地照下来,刺得许知言眼睛生疼,几乎要流出泪来。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下方是川流不息的车海与人潮,城市的喧嚣扑面而来,但他却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无形屏障隔绝在外的幽灵,与这片鲜活的世界格格不入。身体的疲惫尚可忍受,但心里的沉重与混乱,却几乎要将他压垮。
他没有立刻叫车,只是像一具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大脑仿佛一台过载的计算机,各种信息碎片疯狂地冲撞、交织——霍屿那双仿佛能洞穿人心的眼睛,现场照片里赵永诡异的死状,那件透着不祥气息的青铜碎片,衬衫纤维的致命指向,还有三年前那片模糊的火光、剧烈的疼痛以及张海峰最后那张模糊却焦急的脸……所有画面搅在一起,形成一团混沌的漩涡,让他头痛欲裂,几欲呕吐。
不知走了多久,双腿已经麻木,他只是凭借肌肉记忆在移动。直到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才发现自己竟然浑浑噩噩地走回了观澜国际公寓楼下。熟悉的现代化楼宇在夕阳的余晖中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金色的光。
也好,回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是他唯一被“定义”为熟悉、被标注为“安全”的坐标点。
他用指纹和密码打开厚重的防盗门,熟悉的、带着淡淡书卷气和清洁剂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他的领域,他的堡垒。他反手关上门,沉重的“咔哒”落锁声在寂静的玄关回荡。他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全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缓缓地滑坐在地上,将脸埋进膝盖之间。
巨大的无力感和恐慌感如同冰冷的海水,灭顶而来。他不仅没能为自己洗脱嫌疑,反而被拖入了更深的、更黑暗的谜团之中。信任的基石出现了裂痕,这比任何外来的指控都更让他恐惧。
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由金黄变为瑰紫,再渐渐沉入墨蓝。直到双腿因为血液不循环而传来尖锐的麻痛感,他才勉强用手支撑着身体,挣扎着站起来。
霍屿最后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再次在他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记录’。也许……有些细节,被你忽略了。”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他步履有些蹒跚地走进书房,按亮台灯,暖黄色的光线驱散了一室昏暗。他在书桌前坐下,先将今天随身携带、记录了半天经历的录音笔连接电脑,将音频文件备份到标注着今日日期的文件夹里。然后,他移动鼠标,点开了那个存放在电脑硬盘深处、专门用于存储以往所有笔记扫描件和录音备份的加密分区。
里面按照年份、月份、日期,建立了层层叠叠、无比规整的文件夹,像一座庞大的档案库,记录着他从三年前那场事故后,这一千多个日夜里的每一天。这是他存在的证明,是他与遗忘抗争的战场,也是他唯一能把握的“历史”。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像进行学术研究一样,开始系统地重新审视。他并没有盲目地乱翻,而是首先随机抽取了最近几个月,以及一年前、两年前的几个不同时间点的文件夹,点开里面的笔记扫描件和高清照片,仔细浏览内容,比对笔迹的细节、书写习惯、墨水色泽的细微差别。
内容大多千篇一律:工作日志,阅读笔记,简单的起居注,偶尔的外出记录(通常伴有详细的地点、时间和事由),以及身体状况的监测。生活轨迹单调得像一首不断重复的、缺乏韵律的副歌,透着一股刻意维持的平静。
难道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他者”,能够如此天衣无缝地、长时间地伪造他每一天的记录,模拟他的笔迹、语气、甚至情绪状态,而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需要多么可怕的耐心、洞察力和掌控力?这简直是对他整个人生的全面入侵和打败!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书桌的左手边角落。那里,静静地摆放着一个有些年头的深褐色木质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已经微微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许多的许知言穿着深蓝色的硕士服,头戴学位帽,脸上洋溢着明亮而充满朝气的笑容,那是未经磨难、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笑容。他的手臂亲昵地搭在身旁一位中年男子的肩膀上。
那位男子穿着一件普通的皮夹克,面容和蔼,眼神却异常明亮、锐利,透着一种历经世事的通透与温和的关切。他便是张海峰。并非许知言学业上的导师,而是他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两人因许知言研究古代艺术品修复与犯罪痕迹学的交叉领域而结识,张海峰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天赋与执着,以及他身上那种难得的、未被世俗沾染的纯粹。两人常常一壶清茶,就能就某个古代案件的细节或者某件文物的历史背景探讨整个下午。
照片拍摄于他硕士毕业那天,距离那场改变一切的“8·15”案发,仅仅只有三个月。
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抬起,轻轻拂过冰凉的相框玻璃,仿佛能透过这层阻隔,触碰到那段温暖而真实的过去。张叔……如果张叔还在,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一定会用他那种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方式,抽丝剥茧,想办法查明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
可是张叔不在了。死得不明不白,案件悬置多年,成为压在无数人心头的巨石。而他自己,这个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却可笑地成为了新一起血腥命案的头号嫌疑人,连自证清白都显得如此艰难。
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不甘和想要抓住点什么、打破这困局的欲望,在他心中翻涌。他移动鼠标,打开了网页浏览器,在搜索框里,缓慢而郑重地输入了“霍屿海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这几个字。
搜索结果页面迅速刷新。大多是官方发布的案件通报中提到的名字,格式化的文字,看不出任何个人色彩。只有寥寥几条几年前的旧闻短讯,提到了他在某次打击跨境走私犯罪的重大行动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配图是一张模糊的集体表彰大会照片,霍屿站在队伍的边缘角落,身姿挺拔如松,面容在低像素下依然能看出冷峻的轮廓,眼神直视前方,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其中一条简讯的末尾,不经意地提到了一句:“……该同志系我局已故功勋刑警张海峰队长亲手培养的徒弟。”
许知言的目光在那行小字上停留了许久。张叔的徒弟……这个男人,继承了他师父未竟的事业,也背负着师父惨死的谜团。他怀疑自己,审问自己,言辞犀利,手段强硬,可又在最后,给出了那样一个模糊却关键的提醒。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一个为了破案可以不择手段、罔顾细节的冷酷执法机器?还是……一个同样在迷雾中艰难跋涉、试图拼凑出真相碎片,却也被自身情感和执念所困的同行?
他关掉了网页,将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抬手用力揉着发胀刺痛的太阳穴。检查记录……霍屿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还能从哪个角度去检查?
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靠墙而立的那一整排顶天立地的实木书架。书架上,除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艺术图册,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本外观完全一致的皮质笔记本,按照年份和月份严格编码,像一列列沉默的士兵,守卫着他丢失的时光。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构成了这座由文字和声音堆砌起来的、关于“许知言”的编年史。
一个念头,如同暗夜中的闪电,骤然划过他混乱的脑海。
他倏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快,眼前甚至黑了一瞬。他稳住身形,走到书架前,手指沿着书脊缓缓划过,感受着皮质封面带来的细微摩擦感。最后,他的手指停留在标注着“2020”和“8月”的那本笔记上。这是记录着他人生断裂前最后一段完整时光的笔记,是他与那个“完整”的许知言最后的连接。
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抽了出来,分量似乎比其他的都要沉重。走回书桌旁,他几乎是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情,翻开了封面。
里面,是他熟悉又陌生的、事故前的笔迹。相比于现在的工整刻板,那时的字迹更显流畅、灵动,带着个人的情绪和锋芒。记录着正在进行的大型修复项目的每一个突破性进展,与张海峰就某个古代案件现场痕迹模拟的激烈讨论,甚至还有一些关于未来职业规划、想去哪里旅行、想看某场展览的琐碎想法和期待。字里行间,充满了那个“完整”的、鲜活的许知言对生活的无限热情与热爱。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着,停留在8月14日那一页。上面写着:“明日与张叔约好,下午两点去美术馆地下库房,核对最后一批即将外展的文物清单和包装方案。希望流程顺利,能早点结束,晚上还可以拉着他一起去尝尝新开的那家杭帮菜,他念叨糖醋排骨好久了。:)”
后面,甚至还画了一个小小的、轻松的笑脸。
8月15日,那一页是刺眼的空白。
再往后翻,是长达数月的、断断续续的医疗记录,笔迹时而潦草虚浮,时而歪斜扭曲,充满了试图重新连接这个破碎世界的痛苦挣扎与混乱,直到后来,才逐渐稳定成现在这种缺乏个性、追求绝对准确和工整的样子。
强烈的酸楚与难以言喻的悲伤汹涌而上,瞬间冲垮了他努力维持的冷静。他猛地合上笔记,将其紧紧地、用力地抱在胸前,仿佛这样就能隔着一千多个空白的日夜,拥抱住那个曾经鲜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自己,就能从中汲取到一丝来自过去的、坚定而温暖的力量。
不能放弃。
他对自己说,声音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异常清晰。
如果连他自己都放弃了,如果连他都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真实性,那么“许知言”这个人,就真的被这场该死的遗忘和背后那双无形的黑手,彻底地、从里到外地杀死了。
他重新坐回电脑前,挺直了脊背,眼神重新变得专注而坚定。他深吸一口气,仿佛即将开始一场艰苦的战役。这一次,他不再仅仅是浏览,而是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般的偏执和严谨,开始从头、逐字逐句地重新审视最近一个月,甚至更早的所有电子记录和高清笔记照片。他检查每一个电子文件的原始创建日期、最后修改日期、属性信息;他比对不同日期笔记笔迹的起承转合、墨水的浓淡变化、书写时笔尖的压强;他甚至戴上专业监听耳机,反复聆听录音笔里每一段录音的背景环境音,试图从中找出任何一丝不和谐的、被忽略的杂音……
时间在指尖敲击键盘和翻动纸页的细微声响中悄然流逝,窗外的天色早已彻底黑透,城市璀璨的灯火取代了夕阳的余晖。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鼠标滚轮在浏览一张上周的笔记高清扫描件时,动作突然毫无征兆地僵住了。
他的瞳孔猛地收缩,身体前倾,几乎要贴到屏幕上。
他的目光,如同被最精密的磁石吸引,死死地凝固在图片上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那是记录着“查阅古籍,无实质性进展”那一页的右下角,靠近装订线的边缘位置。
在那里,用极淡的、近乎与纸张原色融为一体的H铅笔,以一种极其轻微、仿佛生怕被人察觉的笔触,勾勒出了几个极其微小、结构古怪的符号。
那符号,扭曲,怪异,带着一种古老而邪恶的仪式感。
与他今天上午,在市立美术馆那件诡异的青铜碎片上,透过高倍放大镜才勉强看清的、刻在隐蔽凹陷处的标记,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