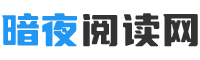故事主线围绕【周砚之】展开的言情小说《寒夜孤灯照前路》,由知名作家“美好永存”执笔,情节跌宕起伏,本站无弹窗,欢迎阅读!本书共计15758字,寒夜孤灯照前路精选章节,更新日期为2025-11-10 15:43:05。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已完结。小说详情介绍:她吓得脸色发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说:“是你骑马太快,差点撞到我,怎么能怪我?”“反了你了!”中年男人扬起手,就要打下去。周砚之赶紧冲上去,抓住他的手腕:“这位老爷,息怒。小姑娘年纪小,不是故意的,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她吧。”中年男人转过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看见他身上打补丁的长衫,还有怀里...
《寒夜孤灯照前路》免费试读 寒夜孤灯照前路精选章节
第一章寒夜煮字光绪十七年,冬。铅灰色的云压在苏州城的檐角上,雪粒子砸在青石板上,
碎成一捧细白的齑粉。周砚之缩在玄妙观西侧的破庙里,就着一盏豆大的油灯,
把冻得发僵的手凑到火苗边烘着。油盏是捡来的粗瓷碗,里面剩的油只够烧半个时辰,
他得赶在灯灭前,把《论语》里“贫而乐”那章的批注写完。庙外传来卖炒货的梆子声,
“笃笃笃”敲在雪夜里,混着寒风钻进破窗棂。周砚之咽了口唾沫,
摸出怀里最后半块干硬的麦饼——那是昨日在巷口帮张屠户写家书,人家给的酬谢。
饼渣子刮得喉咙生疼,他就着融雪水往下咽,目光落回摊在膝头的纸上。纸是最糙的草纸,
边缘起了毛,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连空白处都填着批注。这是他唯一的念想了。三年前,
父亲还是苏州府学的教谕,家里虽不富裕,却也有书房可坐,有暖炉可烘。可一场瘟疫,
父亲没了,母亲也跟着去了,只留下他和一屋子书,
还有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那句:“砚之,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心里有杆秤,
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那时候他还不懂。直到家徒四壁,
连父亲的棺木都得靠乡邻凑钱置办,直到他穿着打补丁的长衫去参加院试,
被同考的富家子弟指着脊梁骨笑“穷酸秀才”,他才懂了“贫”字有多沉,而“乐”字,
又有多难。油灯“噼啪”响了一声,灯花溅在纸上,烫出一个小黑点。
周砚之赶紧用指尖摁灭,心疼地摩挲着纸页——这纸还是上个月在书铺当学徒时,
掌柜的看他可怜,偷偷塞给他的。他深吸一口气,
把冻得发颤的笔蘸了蘸墨——墨是用灶灰和水调的,写在纸上晕得厉害,可总比没有强。
“吱呀”一声,庙门被风吹开,雪粒子灌了进来。周砚之抬头,
看见一个穿着青布棉袍的老者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个布兜,须发上落满了雪。“后生,
能借个地方避避雪吗?”老者声音沙哑,带着些喘息。周砚之赶紧挪了挪身子,
把油灯往旁边递了递:“老丈请坐,这庙虽破,倒还能挡些风。”老者谢了,在他对面坐下,
从布兜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两个热乎乎的肉包子。“后生,看你像是读书人,
想必饿坏了,吃个包子吧。”周砚之脸一红,想推辞,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老者把包子塞到他手里,笑着说:“别客气,我是巷口卖馄饨的王老汉,今日收摊晚了,
遇上这鬼天气。你这是……在温书?”周砚之点点头,咬了口包子,肉馅的香气在嘴里散开,
暖得他眼眶都热了。“是,明年开春就是乡试,想再温习温习。”“乡试好啊,
”王老汉叹了口气,“我那孙子,要是有你一半用功就好了。可惜啊,他总说读书没用,
不如去码头扛活来得实在。”周砚之没接话,只是低头啃着包子。他何尝没动摇过?
上个月在码头帮人搬货,一天能挣五十文钱,够买两斤米,比在书铺当学徒强多了。
可每当他想放下书本,父亲临终前的眼神就会浮现在眼前,
还有那些藏在书里的批注——那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也是他唯一的根。油灯渐渐暗了下去,
王老汉从怀里掏出个小油壶,往碗里倒了些油:“我这油是炸馄饨剩下的,你别嫌弃,
将就着用。”周砚之喉头一紧,想说谢谢,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他看着油灯重新亮起来,
火苗跳动着,映在王老汉布满皱纹的脸上,也映在自己摊开的书页上。“老丈,
”他忽然开口,“您说,读书真的有用吗?”王老汉愣了愣,随即笑了:“后生,
我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我那馄饨摊,要是没了我这双手,就开不下去。
你这读书,就像我揉面,得慢慢来,得用心,揉到了火候,馄饨皮才筋道,煮出来才好吃。
你现在觉得难,是因为火候还没到。”周砚之看着手里的包子,又看了看眼前的老者,
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他低下头,重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贫而不馁,
困而不辍,方为读书人本色。”雪还在下,庙外的梆子声渐渐远了,可破庙里的油灯,
却亮了一整夜。第二章街头偶遇开春的时候,苏州城的雪化了,
巷子里的泥路变得湿漉漉的。周砚之揣着攒了三个月的积蓄——总共两百三十文钱,
去书铺买了一本新的《朱子语类》。这是他准备乡试的重要参考书,
之前一直借的是书铺的旧本,上面的批注密密麻麻,有些地方甚至看不清原文。从书铺出来,
他抱着书,沿着护城河边走。河边的柳树发了新芽,嫩黄的枝条垂在水面上,
荡起一圈圈涟漪。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常带他来这里散步,指着河里的游船,说:“砚之,
你看那些船上的人,有的是为了寻乐,有的是为了谋生。可不管是哪种,心里都得有个方向。
”那时候他不懂,现在却懂了。他的方向,就是考上乡试,考上会试,考上殿试,
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让父亲的心血不白费,为了让那些像王老汉一样的普通人,
能被人看见,能被人尊重。正想着,忽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争吵声。他往前走了几步,
看见一群人围在路边,里面有个穿着绸缎长袍的中年男人,
正指着一个卖花的小姑娘骂:“你这小蹄子,敢挡我的路?我的马受惊了,你赔得起吗?
”小姑娘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穿着打补丁的棉袄,手里提着个篮子,里面的茉莉花撒了一地。
她吓得脸色发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说:“是你骑马太快,差点撞到我,
怎么能怪我?”“反了你了!”中年男人扬起手,就要打下去。周砚之赶紧冲上去,
抓住他的手腕:“这位老爷,息怒。小姑娘年纪小,不是故意的,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她吧。”中年男人转过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看见他身上打补丁的长衫,
还有怀里的书,不屑地笑了:“哪里来的穷酸秀才,也敢管我的闲事?我告诉你,
我是苏州府的盐商张万霖,你再多管闲事,我让你在苏州城待不下去!”盐商?
周砚之心里一沉。苏州的盐商大多有钱有势,寻常百姓根本惹不起。
可他看着小姑娘害怕的眼神,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父亲去世后,他也是这样,
在别人的白眼和呵斥中过日子。“张老爷,”他定了定神,“您是有钱人,可小姑娘卖花,
也是为了糊口。您要是打了她,传出去,对您的名声也不好。不如这样,她篮子里的花,
我买了,就当是给您赔罪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仅有的几十文钱,
递给小姑娘:“这些钱,你拿着,再去进些花,以后小心点,别在路边卖了。
”小姑娘愣了愣,接过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张万霖看着这一幕,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本想发作,可周围的人都在看着,
要是真的跟一个穷秀才计较,反而显得他小气。他冷哼一声,甩开张砚之的手,翻身上马,
绝尘而去。人群散了,小姑娘还跪在地上,不停地道谢。
周砚之赶紧把她扶起来:“快起来吧,别跪着了。以后要注意安全,别在马路上卖花了。
”小姑娘点点头,从篮子里捡起一朵开得最艳的茉莉花,递给他:“公子,这朵花给你,
香香的。”周砚之接过花,放在鼻尖闻了闻,一股清香沁入心脾。
他看着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走了,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他想起父亲说的“心里有杆秤”,
或许,这杆秤,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伸出手,能站出来。他抱着书,继续往前走。
阳光透过柳树的缝隙,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茉莉花,
又看了看怀里的书,忽然觉得,乡试,好像也没那么难了。第三章乡试风波七月,
江南的天气闷热得像个蒸笼。周砚之背着行囊,走进了苏州府的贡院。贡院里挤满了考生,
有的穿着华丽的长衫,身边跟着书童,有的跟他一样,穿着朴素的衣服,
手里只提着一个小包袱。他找到自己的号房,那是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小隔间,
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炉子。他把行囊放好,拿出笔墨纸砚,
还有从王老汉那里借来的小锅——王老汉知道他要参加乡试,特意把家里的小锅借给了他,
还塞了一袋米和几个鸡蛋,说:“后生,好好考,等你中了举,我请你吃馄饨。
”乡试考三场,每场考三天。第一场考的是“四书”义,题目是“子曰:‘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周砚之看到题目,心里一松。这章他熟,不仅熟原文,还熟各家的批注,
甚至自己也写过好几篇读后感。他铺开纸,磨好墨,先在草稿纸上打了个提纲,
然后开始动笔。他写得很顺,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仿佛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涌出来。
他想起父亲教他的写作方法:“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情真意切,不能空洞无物,
也不能堆砌辞藻。”他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对“学而时习之”的理解,都融入到文章里,
写得酣畅淋漓。可到了第二天,麻烦来了。他隔壁的考生是个富家子弟,叫李修远,
是苏州知府的外甥。李修远平时不怎么读书,全靠作弊来应付考试。
他看见周砚之写得那么快,心里嫉妒,就故意把墨汁洒到周砚之的纸上。“哎呀,不好意思,
手滑了。”李修远假惺惺地说。周砚之看着自己写了一半的文章被墨汁弄脏,心里又气又急。
这可是乡试,一场定输赢,要是文章被弄脏了,轻则扣分,重则作废。他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里的火气:“李公子,请你下次小心点。”李修远却不以为意,
反而嘲讽道:“穷酸秀才,就算你写得再好,也中不了举。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周砚之没理他,赶紧拿出备用的纸,重新开始写。
可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只能加快速度,连午饭都没顾上吃,一直写到傍晚,才把文章写完。
交卷的时候,他看见李修远手里拿着一张小抄,正偷偷地往袖子里塞。他皱了皱眉,
想说什么,可又想起父亲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他咬了咬牙,转身离开了号房。
回到住处,他累得倒头就睡。可夜里,他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李修远的嘴脸,
想起自己被弄脏的文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努力,到底有没有用?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他想起了王老汉的话:“读书就像揉面,得慢慢来,得用心,
揉到了火候,馄饨皮才筋道。”他想起了那个卖花的小姑娘,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眼神。
他猛地坐起来,在心里对自己说:“周砚之,你不能放弃。就算这次考不上,
你也要坚持下去。因为你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那些相信你的人,为了心里的那杆秤。
”第三天,考的是策论,题目是“如何解决江南的水患问题”。周砚之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
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去过江南的农村,亲眼见过水患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他还读过很多关于治水的书籍,比如《水经注》《河防一览》等。他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
还有书本上的知识,写了一篇策论。他在文章里提出,要治理江南水患,不能只靠修堤坝,
还要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同时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机制,让百姓能提前做好准备。
他还建议,**要减轻百姓的赋税,让百姓有能力参与到治水中来。写这篇策论的时候,
他仿佛看到了江南的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看到了一片片丰收的稻田,
看到了孩子们在田埂上奔跑嬉戏。他写得情真意切,泪水甚至打湿了纸页。三场考试结束,
周砚之走出贡院,感觉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他抬头看了看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
他想起了王老汉的馄饨摊,想起了护城河边的茉莉花,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第四章金榜题名九月,是放榜的日子。苏州府的贡院外挤满了考生和百姓,
大家都在翘首以盼,想知道今年的举人名单里,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周砚之站在人群后面,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他手里攥着王老汉给他的一个热乎乎的馄饨,
那是王老汉一大早就起来做的,特意送来给她的。“后生,别紧张,不管中不中,
你都是好样的。”王老汉拍着他的肩膀说。放榜的官差来了,他们拿着一张大红纸,
贴在贡院的墙上。人群一下子涌了上去,挤得水泄不通。周砚之个子不高,根本看不见。
他只能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努力地往里面看。“李修远!李修远中了!”人群里有人喊道。
周砚之心里一沉。李修远那样的人都能中举,那自己呢?他是不是真的像李修远说的那样,
就算写得再好,也中不了举?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周砚之!
周砚之中了!第三名!”他愣了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挤开人群,跑到榜前,
顺着名字往下找。找到了!在第三名的位置,赫然写着“周砚之”三个字。他看着那三个字,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三年了,整整三年,他忍饥挨饿,受尽白眼,就是为了这一天。
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王老汉,想起了那个卖花的小姑娘。
他终于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后生,你中了!你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