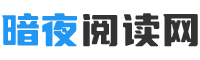由知名作家“亨通西区”创作,《墨耳祭》的主要角色为【墨耳沈清辞】,属于言情小说,情节紧张刺激,本站无广告干扰,欢迎阅读!本书共计19910字,墨耳祭精选章节,更新日期为2025-11-21 10:53:10。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已完结。小说详情介绍:就像墨耳的一生,朴素而真挚。“墨耳,今年的菊花开得比往年都好。”老人轻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支早已秃了的毛笔,笔杆上有一道浅浅的凹痕,像是被什么动物长期啃咬留下的。他的手指摩挲着那道凹痕,仿佛能透过时光,触摸到那个毛茸茸的脑袋,那双温顺而聪慧的大眼睛。五十三年了。他官至礼部侍郎后请辞还乡,回到这小村庄...

《墨耳祭》免费试读 墨耳祭精选章节
暮色四合,八十三岁的沈清辞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小屋后的坟前。坟上已长满青草,
四周的野菊开得正盛,在微凉的秋风中轻轻摇曳。这些野菊是他每年清明时节亲手种下的,
如今已自成一片花海,年年岁岁,花开不败。他缓缓坐下,布满老年斑的手轻抚墓碑,
上面只刻着两个字:墨耳。这墓碑是他亲手所刻,没有冠冕堂皇的谥号,没有冗长的墓志铭,
就像墨耳的一生,朴素而真挚。“墨耳,今年的菊花开得比往年都好。”老人轻声说着,
从怀中掏出一支早已秃了的毛笔,笔杆上有一道浅浅的凹痕,
像是被什么动物长期啃咬留下的。他的手指摩挲着那道凹痕,仿佛能透过时光,
触摸到那个毛茸茸的脑袋,那双温顺而聪慧的大眼睛。五十三年了。
他官至礼部侍郎后请辞还乡,回到这小村庄,守着一座孤坟,度过了大半生。外人不解,
同僚惋惜,唯有他明白,没有墨耳,就没有他沈清辞的今天。
那些在朝堂上侃侃而谈的治国方略,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坚持,其根底,
都源于一头驴教会他的东西——关于尊严,关于情义,关于生命最本真的价值。
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记忆也随之延伸,回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的风,
比现在冷得多;那时的雪,比现在大得多;那时的他,
还是个一无所有、前途渺茫的落魄秀才,只有一头驴,愿意与他相依为命。
第一章落第嘉靖十七年冬,北京城外的官道上,一辆破旧的驴车在风雪中艰难前行。
驴车极其简陋,车辕已有裂痕,轮子转动时发出吱呀作响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车上堆着两个旧书箱和一个单薄的铺盖卷,除此之外,再无长物。
赶车的青年约莫二十五六岁,面容清瘦,眉宇间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文气,
但更多的却是掩饰不住的疲惫与失落。他裹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色棉袍,
可刺骨的寒风还是无孔不入地钻进来,冻得他手指僵硬,几乎握不住缰绳。
这青年便是沈清辞,字文远,江南湖州府安吉县人氏。这是他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
也是第三次名落孙山。“墨耳啊,又要陪我回去了。”沈清辞轻叹一声,
呵出的气在眼前凝成一团白雾。他伸手摸了摸身旁这头名叫墨耳的驴的脖颈。墨耳通体灰色,
唯独左耳长着一块形状奇特的墨黑色胎记,仿佛是谁不小心洒上的浓墨。
它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转过头用温顺的大眼睛看了看沈清辞,发出一声轻微的鼻响,
像是在安慰。这头驴是三年前他第一次进京赶考前,病重的父亲用家中最后一点积蓄买的。
父亲拉着他的手说:“辞儿,爹没什么能留给你的,这驴看着有灵性,左耳的胎记像墨点,
是文曲星的兆头,你叫它墨耳吧。让它陪着你,上路也有个照应。”父亲去世后,
墨耳就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陪着他三次北上南下,走过了几万里路途。风雪越来越大,
密集的雪片扑打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道路渐渐被积雪覆盖,墨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速度越来越慢。沈清辞见前方有处突出的山岩可以暂避风雪,便轻轻拉动缰绳。“墨耳,
我们去那边歇歇。”他将驴车赶到山岩下,这里果然风力小了许多。他跳下车,
先从书箱里找出一块旧油布,仔细盖在书箱上,怕雪水浸湿了里头的书籍文稿。
然后才从行囊中取出最后半块又干又硬的炊饼,掰了一小块放进自己嘴里,
又掰了稍大的一块,递到墨耳嘴边。“吃吧,你也饿了一天了。”墨耳犹豫了一下,
看看沈清辞手中的饼,又看看他消瘦的面颊,才轻轻从他手中叼过饼块,慢慢地咀嚼起来。
沈清辞知道,墨耳这是心疼粮食,想让他多吃点。他心头一暖,伸手抚摸着墨耳的脸颊。
待一人一驴分食了那半块饼,沈清辞从书箱中取出一卷策论,那是他考前精心准备的,
自以为切中时弊,文采斐然,本以为这次一定能中。他清了清嗓子,
开始对着墨耳读起来:“夫治国之道,在富民、在教民、在安民。今之弊政,
在于赋税繁重而民不聊生,吏治腐败而贤路壅塞...”他的声音在风雪中显得微弱,
但每一个字都读得认真。这些年来,他习惯了对着墨耳读书、写作。这头不会说话的驴,
总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甩甩耳朵,仿佛在思考文中的深意。在沈清辞看来,
墨耳比那些嘲笑他迂腐的乡邻更能理解他的抱负。“...故曰:欲治国者,
必先恤民;欲恤民者,必先选贤。贤者,非必出自豪右,寒门亦多俊杰...”读到这里,
沈清辞的声音低了下来,最终化为一声长叹。他放下文稿,苦笑着摸了摸墨耳的头,
“我是不是很可笑?明明连个进士都中不了,还整天想着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墨耳用头轻轻蹭了蹭他的手臂,然后挪动身体,为他挡住从侧面吹来的寒风。
这个细微的举动让沈清辞眼眶发热。他记得第二次落第回乡时,途中染了风寒,高烧不退,
也是墨耳将他拖到一处破庙,又不知从哪里叼来一些干草盖在他身上,陪了他两天两夜,
直到他退烧。“还好有你,墨耳。”沈清辞将额头抵在墨耳温暖的脖子上,轻声说。
夜幕降临,风雪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气温急剧下降,沈清辞冷得浑身发抖。
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过夜,否则真会冻死在这荒山野岭。
他试图起身,却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差点摔倒。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滚烫。糟糕,
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起高烧。他强撑着将驴车拴好,从行李中取出唯一的薄毯,
不是裹在自己身上,而是仔细地盖在墨耳的背上。“你不能冻着,我们还指望你拉车回家呢。
”他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说服自己。墨耳不安地扭动身体,想把毯子甩下来还给他,
但沈清辞按住了。“听话。”他声音虚弱,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深夜,
沈清辞的体温越来越高,意识开始模糊。他知道这样下去凶多吉少。在完全昏迷前,
他用尽最后力气,解开了系在树上的缰绳,拍了拍墨耳。“走吧,你自己逃命去吧,
别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说完这句,他便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救主沈清辞做了一个漫长而混乱的梦。他梦见自己金榜题名,骑马游街,
好不风光;又梦见父亲还活着,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儿有出息”;还梦见儿时的玩伴,
那些曾经一起读书、一起畅谈理想的少年,如今各奔东西,有的早已考取功名,
有的转而经商致富,唯有他,还在科举的路上艰难前行。
“水...水...”他干裂的嘴唇翕动着,感到喉咙像着了火一样灼痛。朦胧中,
有什么温暖湿润的东西在舔舐他的脸颊。沈清辞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
发现墨耳正用头反复蹭他的脸,见他醒来,墨耳发出低低的叫声,
咬住他早已被雪水浸湿的衣角,试图拉他起身。“墨耳...你没走?”沈清辞虚弱地问,
不敢相信在生死关头,这头驴竟然选择留下来陪他。墨耳固执地扯着他的衣角,
方向明确地引着他往山坳里走。沈清辞强撑着爬起来,扶着驴背,踉跄跟上。他浑身无力,
几乎将全身重量都压在了墨耳身上。墨耳没有丝毫不耐,稳稳地支撑着他,
在及膝的积雪中艰难前行。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他们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
洞口被枯藤半掩着,里面虽然阴暗,但比外面暖和得多,至少没有刺骨的寒风。
墨耳把他推进洞里,自己却转身要走。“墨耳!”沈清辞惊慌地喊道,声音嘶哑。
经历了被抛弃的恐惧后,他再也承受不起失去这唯一伙伴的痛苦。墨耳回头看了他一眼,
眼神温和而坚定,仿佛在说“相信我”,然后毅然冲回了风雪中。山洞里,
沈清辞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高烧让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在清醒的片刻,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墨耳的情景。那是嘉靖十四年的春天,父亲已经病重卧床半年。
家中本就清贫,为给父亲治病,能卖的都卖了,只剩下几亩薄田和这座祖传的老宅。那天,
父亲突然精神好了许多,把他叫到床前,塞给他一个破旧的钱袋。“辞儿,爹没用了,
这些钱你拿着,去买头驴。你要进京赶考,不能没有代步的。”父亲咳嗽着说,
“村东头老张家的驴下崽了,你去挑一头好的。”他记得自己当时不肯要,
说要把钱留给父亲抓药。父亲却罕见地动了怒:“你要气死我吗?我这病是治不好的了,
但你的人生还长!听爹的话,去!”他含着泪去了老张家。驴圈里有三头小驴驹,
两头活蹦乱跳,争抢着母驴的奶头。只有最瘦小的一头,安静地站在角落,
左耳上一块明显的黑色胎记,像极了一滴浓墨。老张说这头最弱,便宜卖给他。
他却鬼使神差地选了这头,因为它看他的眼神,不像牲畜,倒像是个懂事的孩子。
他牵着驴回家,父亲躺在床上,远远看到驴耳上的胎记,竟然笑了:“好,好,这驴有文气,
是文曲星的兆头。你叫它墨耳吧,陪你读书上路。”半个月后,父亲去世了。
丧事办得极其简单,沈清辞跪在坟前发誓,一定要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然而命运弄人,
连续三次落第,他成了乡邻眼中的笑柄。“爹,儿子没用...”沈清辞在昏迷中喃喃自语。
不知过了多久,洞外传来脚步声和人声。沈清辞勉强睁眼,
看到墨耳引着一个猎户打扮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墨耳的左耳有一道新鲜的伤口,
鲜血已经凝固在黑色的胎记上,显得格外刺眼。它的身上也多了几处擦伤,
走路时后腿微微颤抖,显然经历了极大的艰辛。“这畜生真有灵性,
”猎户边说边查看沈清辞的状况,“半夜撞我家门,我以为是野狼,出来打它一棍,
它疼得直哆嗦,却不逃走,只是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哀求。我看它通人性,就跟着它来了。
公子,你冻得不轻啊。”沈清辞没有先回应猎户,而是伸手抱住墨耳的脖子,
眼泪无声地流下,滴在墨耳受伤的耳朵上:“你若会说话,定是我唯一的知己。
”猎户将几乎虚脱的沈清辞扶上自己的马,牵着墨耳,回到了半山腰的猎户小屋。猎户姓王,
独居在此,以打猎为生。他给沈清辞熬了驱寒的汤药,又拿出干粮让他果腹。
沈清辞在王家休养了三天。期间,墨耳始终守在门外,不肯远离。
沈清辞把王猎户给的干粮分一半给墨耳,自己只吃个半饱。“你这驴比有些人还强。
”王猎户感叹道,“那眼神,通人性得很。我打猎二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驴。
”沈清辞轻轻抚摸墨耳受伤的耳朵,低声道:“它不只是驴。”第三天,沈清辞的身体好转,
决定继续上路。王猎户送了他一些干粮和一件旧皮袄,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就当是赔你这驴的伤。”王猎户拍拍墨耳的头,“好驴啊,好好待它。
”沈清辞深深一揖:“王大哥救命之恩,清辞没齿难忘。”“快上路吧,
趁着这几天雪小了些。”王猎户挥挥手。沈清辞没有骑驴,而是牵着墨耳,
一步步向山下走去。走出很远,回头望去,王猎户还站在小屋前,朝他们挥手。
而墨耳也回头望了望,发出一声低鸣,仿佛也在道别。返乡的路途漫长而艰辛,
但有了皮袄保暖和干粮果腹,加上沈清辞的身体逐渐恢复,他们终于在腊月二十三,
小年前一天,回到了江南老家沈家村。村口的槐树下,几个孩童正在玩耍。
见到骑着驴、衣衫褴褛的沈清辞,他们立刻编起歌谣唱道:“沈秀才,又落第,
骑着毛驴回乡里~三年考,三年空,不如回家种田地~毛驴叫,墨耳听,秀才哭,
泪涟涟~”沈清辞低着头,假装没听见。墨耳却突然朝孩童们方向喷了个响鼻,跺了跺蹄子,
吓得他们一哄而散。回到家中破旧的老宅,沈清辞把墨耳牵进简陋的驴棚,添上草料,
又打来清水,轻声道:“到家了,墨耳。”墨耳用头轻轻蹭了蹭他的胸口,
像是在说“回来就好”。那一晚,沈清辞睡得格外踏实。梦中没有金榜题名,没有锦衣还乡,
只有一头驴,安静地陪在他身边,眼神温和而忠诚。第三章谋生返乡后的日子清贫而简单。
沈清辞的老宅位于村西头,是三间低矮的瓦房,因年久失修,每逢雨天就到处漏水。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和一口水井,角落搭了个简陋的驴棚,这就是他和墨耳的全部家当。
家中早已一贫如洗,沈清辞不得不面对最现实的问题:如何活下去。他试过开馆授徒,
但村里适龄的孩童本就不多,且大多帮家里干农活,能来读书的寥寥无几。
他也试过下地种田,但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插秧割稻的活计实在力不从心。最后,
他决定在村口摆个代写书信的小摊。第一天出摊,沈清辞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了。
他先给墨耳添了草料,自己简单吃了点昨晚剩下的粥,
然后将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和文房四宝搬上驴车。墨耳似乎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乖乖站着让他套上车辕。“墨耳,从今往后,咱们就靠这个过日子了。
”沈清辞拍拍墨耳的脖子,语气中带着几分忐忑。村口有棵大槐树,
树下是村民们日常聚集闲聊的地方。沈清辞将小桌摆好,铺开一块白布,
上面用毛笔写着“代写书信”四个字。起初,村民们只是远远观望,没人上前。这也难怪,
沈清辞连续三次落第,在村民眼中已是“无用”的象征,加上他平时不善交际,
更让人觉得清高孤傲。眼看日上三竿,还是一桩生意没有,沈清辞心中焦急,却强作镇定,
拿出本书读起来。墨耳安静地卧在一旁,偶尔甩甩尾巴,驱赶苍蝇。快到中午时,
同村的张寡妇怯生生地走过来:“沈...沈秀才,能帮俺写封信不?俺儿子在城里做学徒,
快一年没音讯了...”“当然可以。”沈清辞连忙起身,铺开信纸,“您慢慢说,
我帮您写。”张寡妇识字不多,表达也颠三倒四,但沈清辞没有丝毫不耐烦,
仔细询问她儿子的情况和要交代的事情,然后用通俗易懂又得体的文字写下来。写完后,
还一字一句念给张寡妇听。“...儿在外务必保重身体,勿以家为念。娘一切安好,
唯望我儿勤勉做事,诚实为人...”念到这里,张寡妇已经泪流满面,“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沈秀才,你写得真好!”沈清辞只收了两个铜板,远低于市价。
张寡妇千恩万谢地走了。这成了当天的唯一一桩生意,但却为沈清辞打开了局面。此后,
村民们渐渐发现,这个看似清高的秀才其实和气得很,代写书信不仅字迹工整、文笔流畅,
而且收费极低,对穷苦人家甚至分文不取。沈清辞的小摊前渐渐有了人气。每天清晨,
沈清辞都会带着墨耳到村头的老槐树下摆摊。他写信时,墨耳就安静地卧在一旁,时间长了,
村民们也习惯了这头特别通人性的驴。有次,一个外来的顽童想偷摊上的笔墨,
墨耳突然站起来,发出威胁的低吼,把那孩子吓跑了。“你也知道护着我的生计了。
”沈清辞笑着抚摸墨耳的头,从怀中掏出一小块麦糖奖励它。
这是他们之间的小秘密——每次沈清辞写完一篇文章,都会让墨耳舔舔笔尖上的墨迹,
说是让它也“尝尝墨香”,然后奖励它一点甜头。墨耳似乎很享受这个仪式,
每次都会眯起眼睛,细细品味墨汁中那一点若有若无的甜味。日子一天天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