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泡芙和可乐”精心打造的言情小说《咸鱼小职员竟是豪门失踪千金》,描写了色分别是【林雅琴文仲渊文夏阳】,情节精彩纷呈,本站纯净无弹窗,欢迎品读!本书共计19842字,咸鱼小职员竟是豪门失踪千金精选章节,更新日期为2025-08-22 12:15:30。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已完结。小说详情介绍:从未停止!只是……”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只是,文家内部……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他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确认无人,才走回来,声音压得更低。“文先生当年,是白手起家,文氏是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但家族大了,人心就杂。林夫人……是文先生的原配夫人去世五年后续娶的。她嫁进来时,带着和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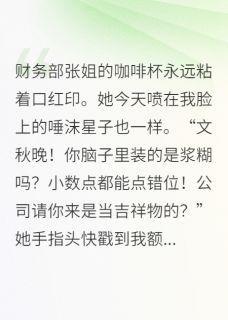
《咸鱼小职员竟是豪门失踪千金》免费试读 咸鱼小职员竟是豪门失踪千金精选章节
财务部张姐的咖啡杯永远粘着口红印。她今天喷在我脸上的唾沫星子也一样。“文秋晚!
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小数点都能点错位!公司请你来是当吉祥物的?
”她手指头快戳到我额头,“重做!下班前交不上来,明天就给我抱着纸箱子滚蛋!
”办公室静得像坟场。隔壁工位的小米缩着脖子,假装自己是个鹌鹑。
我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感觉它们都在跳舞。手指冰凉。这份报表关乎季度审计,
错一个小数点,连锁反应能掀翻半个部门。张姐的骂声还在耳朵里嗡嗡响。
手机突然在兜里疯狂震动,屏幕亮着“未知号码”。“喂?”我压低声音,弓着背,
尽量把自己缩进格子间挡板后面。“文秋晚女士吗?”一个男声,冷硬得像块铁板。“我是。
”“请您立即下楼一趟。现在。正门口黑色宾利。”“你谁啊?推销保险还是催网贷?
我没钱!”我有点烦,报表像山一样压着。“事关您的身世。”那声音顿了一下,“以及,
文仲渊先生的生命。”文仲渊?这名字像颗炸弹,扔进了我二十五年平静得像死水潭的人生。
财经新闻里常出现。文氏集团。那个传说中富可敌国、跺跺脚能让半个城市晃三晃的文家。
我脑子空白了一瞬。“神经病。”我嘟囔着,想挂。“您右肩胛骨下方,靠近脊柱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块浅褐色的胎记?形状像一片小叶子。”那声音又快又稳,
像在念一份确认无误的报告。我后背猛地一僵。那块胎记,只有我妈知道。
她总说那是老天爷给我盖的戳儿。我妈去年走了。肺癌。“你……你到底是谁?
”“我在楼下等您。五分钟。过时不候。”电话断了。忙音。冰冷的,单调的。
我坐在格子间里,像被冻住了。张姐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过来,指关节敲在我隔板上,
梆梆响。“发什么呆!报表呢文秋晚?等着我请你吃晚饭吗?”我猛地站起来。
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整个办公室的目光唰地钉在我身上。“张姐,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飘,“我…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出去?
”张姐的细眉毛挑得快飞进发际线,“报表做完了?你想去哪?给我坐下!”“急事!
”我抓起那个屏幕碎成蜘蛛网的旧手机,还有桌上啃了一半的冷包子,“人命关天!
”没等她再咆哮,我拔腿就跑。冲出压抑的格子间,冲进电梯,按下1楼。
电梯镜子里映出我的脸。苍白的,头发有点乱,黑框眼镜滑到了鼻尖,
身上是洗得发白的旧衬衫。一个标准的、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社畜。文仲渊?身世?
像一场荒诞离奇的梦。可那块胎记…像一根冰冷的针,扎破了所有侥幸。楼下,
一辆线条冷硬、黑得能照出人影的宾利,嚣张地横在公司大门口。保安站在旁边,
想拦又不敢拦的样子。车窗降下一半。驾驶座上的男人,穿着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寸头,
侧脸线条像刀削出来的。他转过脸,眼神锐利得像鹰隼,上下扫了我一眼。“文秋晚**?
”我点头,喉咙发干。“上车。”语气不容置疑。我拉开车门,
一股清冷的皮革混合着某种昂贵木质香的味道扑面而来。
和办公室里常年弥漫的廉价咖啡味、外卖油味截然不同。车子无声地滑出去,汇入车流。
男人没看我,专注开车。“我是陈默。文先生的安全顾问。”他递过来一个平板电脑,
屏幕亮着。上面是一份密密麻麻的报告。标题刺眼:《DNA亲缘关系鉴定报告》。
委托方:文仲渊。检材1:文仲渊(血液)。检材2:文秋晚(口腔拭子样本)。
鉴定意见:依据DNA分析结果,支持文仲渊是文秋晚的生物学父亲。我盯着那行字,
每个字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却像天书。“口腔拭子?”我猛地抬头,声音发颤,
“你们什么时候……”“上周,您在公司楼下那家‘好运来’快餐店吃饭。
”陈默的声音毫无波澜,“您点了一份特价黄焖鸡米饭。服务员不小心碰掉了您的水杯,
给您递纸巾擦水时,回收了您用过的纸巾。”我想起来了。那个年轻的服务员,手忙脚乱,
一脸歉意。那张沾了我唾液的纸巾。原来那不是意外。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这…这不可能!”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我妈叫李秀芬!她就是个普通女工!
我爸……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工伤没了!我叫文秋晚,是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是秋天,
傍晚!”“李秀芬女士,是您养母。”陈默语气依旧平稳,像在陈述一个既定事实,
“二十五年前,文家唯一的女儿,刚满三个月,在文夫人带她去打疫苗的路上,被绑架。
绑匪索要巨额赎金,文先生报了警。但绑匪极其狡猾,中途换了数次交易地点,
最后……彻底失去了消息。”车窗外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飞速倒退,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文先生和夫人从未放弃寻找。悬赏金额高到足以让任何人疯狂。直到去年,
我们追查到当年一个绑匪的远房亲戚,那人临终前说出,当年绑匪头子带着孩子逃窜时,
在邻省一个小镇突发重病,眼看不行了。他怕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就把孩子丢在了镇卫生院门口。”邻省小镇……卫生院……我妈的老家!她确实说过,
我是她在镇卫生院门口捡到的弃婴。“我们找到了当年卫生院的一些模糊记录,
锁定了几位可能的知情老人。最终,一位已经有些糊涂的老护士长提到,那年深秋,
卫生院门口确实被放了个女婴,裹着很旧的薄毯子,哭得都没力气了。
后来被一个在镇上打零工、叫李秀芬的年轻女人抱走了。”每一个细节,
都像一块沉重的拼图,严丝合缝地嵌进了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我妈,李秀芬,
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工。她总说我是老天爷看她可怜,送给她的宝贝。她没日没夜地干活,
供我读书,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去年她咳嗽咳出血,还瞒着我,硬撑着,
直到倒下就再没起来。临终前,她紧紧抓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看着我,
一遍遍说:“晚晚…好好的…妈对不起你…没能给你…好日子…”她是不是知道什么?
她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心口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我喘不上气。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大颗大颗砸在平板的屏幕上,晕开了那份冰冷的鉴定报告。
陈默递过来一盒纸巾,没说话。车子驶入一片我从未踏足过的区域。
高大的树木掩映着深宅大院,空气都变得安静而昂贵。
最终停在一栋灯火通明、宛如城堡的巨大别墅前。巨大的雕花铁门无声滑开。
一个穿着深色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人已经等在那里,表情严肃得像块石头。
“文**,我是管家周梅。”她微微躬身,动作标准得像量过,“请跟我来。
”别墅里的奢华超出我的想象。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巨大的水晶吊灯,
墙上挂着的看不懂但感觉很贵的画。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合着花香。
周管家步履匆匆,高跟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声音。她推开一扇厚重的双开门。巨大的卧室。
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更浓了。房间中央,一张宽大得离谱的床上,躺着一个老人。
身上连着各种仪器管子,屏幕上跳动着曲折的线条和数字。他瘦得脱了形,脸色灰败,
眼窝深陷,只有微弱的呼吸证明他还活着。文仲渊。
财经杂志封面上那个意气风发、眼神锐利的商业巨鳄。此刻像一截枯朽的木头。
床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保养得宜、穿着昂贵丝绒长裙的女人,五十岁上下,妆容精致,
但眉眼间有掩不住的疲惫和焦虑。她旁边是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穿着潮牌,
头发染成亚麻色,耳朵上好几个亮闪闪的耳钉,正不耐烦地划拉着手机。“林夫人,
夏阳少爷。”周管家声音平板地介绍,“这位是文秋晚**。”那女人——林雅琴,
文仲渊的续弦,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瞬间聚焦在我脸上。那眼神极其复杂。震惊、审视、怀疑,
还有一丝……冰冷的敌意?她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
指甲几乎要掐进我肉里。“你…你就是秋晚?”她的声音带着点颤,眼圈瞬间红了,
泪水说来就来,“天可怜见!老文念叨了二十多年,总算把你找回来了!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她把我往床边拉。那个叫文夏阳的年轻男人终于舍得把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
吊儿郎当地扫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和烦躁。“啧,还真找回来了?
”他撇撇嘴,声音不大不小,“爸都这样了,找回来有什么用?添乱。”“夏阳!胡说什么!
”林雅琴立刻呵斥他,转头对我挤出笑容,眼泪还挂在睫毛上,“秋晚,别介意,
你弟弟被我们宠坏了,口无遮拦的。”弟弟?我看着文夏阳那张写满“我很不爽”的脸。
胃里一阵翻腾。林雅琴拉着我,非要**近床边看文仲渊。那张枯槁的脸近在咫尺,
带着垂死的暮气。旁边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像在倒计时。“爸,”林雅琴俯身,
对着昏迷的老人哽咽着说,“你看看,晚晚回来了!你睁开眼看看啊!”文仲渊毫无反应。
文夏阳嗤笑一声,又低头玩手机去了。周管家端着一个精致的托盘进来,
上面放着一小碗深褐色的中药,热气腾腾。“夫人,先生的药熬好了。”“给我吧。
”林雅琴伸手去接。文夏阳却突然凑过来,动作幅度很大,
胳膊肘“不小心”猛地撞在我端着的药碗上!滚烫的药汁瞬间泼洒出来!我下意识地缩手。
“哗啦!”瓷碗摔在大理石地面上,碎裂声格外刺耳。浓重苦涩的药味瞬间弥漫开来。
深褐色的汁液溅上了我廉价的裤脚和鞋子。“哎呀!”文夏阳夸张地叫了一声,
一脸“无辜”,“姐,你没事吧?怎么这么不小心?这药可贵了!”林雅琴脸色一变,
立刻去看文仲渊有没有被惊扰,又转头瞪了文夏阳一眼:“夏阳!”然后才看向我,
语气带着点不易察觉的责备:“秋晚,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你爸的药不能断的!周管家,
快!再去熬一碗!”周管家面无表情地应声,蹲下去收拾碎片。我站在原地,
裤脚湿漉漉地贴着皮肤,有点烫。看着地上那滩药渍和碎片。看着林雅琴那虚伪的焦急。
看着文夏阳眼底那抹得逞的、恶劣的笑意。心一点点沉下去。这地方。金光闪闪。冰冷刺骨。
这里没有欢迎。只有无声的硝烟。周管家把我领到了三楼一个房间。“文**,
这是您的房间。衣柜里有准备一些衣物,您先休息。晚餐七点开始。”她公式化地说完,
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房间很大,很华丽。巨大的落地窗对着花园。
衣帽间里挂满了崭新的、带着吊牌的名牌衣服。浴室大得能跳舞。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我坐在松软得能陷进去的欧式大床上,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不真实。
裤脚上那块深褐色的药渍已经干了,硬邦邦的,散发着苦味。提醒我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是梦。
我拿出那个屏幕碎得像蜘蛛网的旧手机。点开相册。里面全是和我妈的合影。
她抱着小小的我,在简陋的出租屋前笑。她站在我小学毕业典礼上,
穿着她最好看的那件蓝布褂子。她送我上大学,在火车站,偷偷抹眼泪……最后一张,
是在医院。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戴着氧气罩,努力对我笑。我摩挲着冰冷的屏幕。妈,
我找到“根”了。可这“根”,又冷又硬,带着刺。我该怎么办?晚餐时间到了。
巨大的长条餐桌,亮得能照出人影。林雅琴坐在主位旁边(主位空着,留给文仲渊)。
文夏阳坐在她对面,依旧在玩手机。我被安排在文夏阳旁边。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
很多我叫不出名字。佣人悄无声息地上菜、倒水。气氛沉闷得让人窒息。“秋晚啊,
”林雅琴拿起银筷子,脸上又挂起了那种无懈可击的、慈爱的笑容,“多吃点,看你瘦的。
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还好。”我低头,
看着盘子里那块切得方方正正、像艺术品一样的牛排。“哎,你养母…李女士,也是个好人。
”她叹了口气,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唏嘘,“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可惜,福薄了点。
”她话锋一转,“不过现在好了,你回家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缺什么,想要什么,
跟周管家说,或者直接跟阿姨说。”她夹了一块鲍鱼放到我面前的碟子里。“谢谢阿姨。
”我没动那块鲍鱼。文夏阳终于放下手机,叉起一大块牛排塞进嘴里,嚼得很大声。
他斜眼瞟着我:“喂,听说你之前在那个什么破公司当小财务?一个月挣多少?五千?六千?
”“四千二。”我平静地回答。“噗——”他差点喷出来,随即爆发出一阵毫不掩饰的嘲笑,
“四千二?哈哈哈哈哈!还不够我买双鞋的!真是开了眼了!你这种水平,回来能干嘛?
等着分家产啊?”“夏阳!”林雅琴沉下脸,“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我说错了吗?
”文夏阳梗着脖子,一脸不服,“爸躺那儿人事不省,公司里一堆事,
她一个只会做错报表的小财务,回来不是添乱是什么?妈,你别告诉我你真打算让她进公司?
”林雅琴没说话,只是疲惫地揉了揉眉心。“秋晚,”她看向我,语气温和,
“别听你弟弟瞎说。公司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熟悉环境,陪陪你爸。
他要是知道你回来了,说不定……”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希望渺茫。“对了,
”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你刚回来,身上也没什么钱吧?阿姨先给你转点零花。
”她拿起手机,优雅地点了几下。我放在桌上的旧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
一条银行短信通知。“您尾号*账户收到转账1,000,000.00元。余额1,
000,012.34元。”一百万。后面跟着我那可怜巴巴的余额。强烈的讽刺感。
我盯着那串数字。“谢谢阿姨。”我抬起头,看着她,“不过不用了。我自己有手有脚,
能挣钱。”林雅琴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文夏阳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一百万都嫌少?
胃口不小啊!”“夏阳!”林雅琴这次语气重了些。她重新看向我,笑容更深,
眼神却更冷:“秋晚,跟阿姨还客气什么?这钱你拿着,去买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嘛,
总要打扮打扮。明天让周管家安排司机,带你去逛逛商场。”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
我早早离席,回到了那个华丽冰冷的房间。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被精心打理过的花园。
一百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账户里。林雅琴的“好意”。文夏阳的敌意。
昏迷不醒的父亲。这潭深不见底的水,比我想象的更浑。夜里。
整栋别墅安静得像一座巨大的坟墓。只有走廊深处偶尔传来仪器微弱的滴滴声。我毫无睡意。
白天文夏阳撞翻药碗时,林雅琴那一瞬间的眼神,冰冷又锐利。她为什么那么紧张那碗药?
仅仅是怕耽误治疗?还是……一个念头冒出来,让我自己都打了个寒颤。
我轻手轻脚地溜出房间。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吸走了所有脚步声。凭着白天的记忆,
我摸索到二楼文仲渊书房的位置。门锁着。我试了试把手,纹丝不动。就在我准备放弃时,
目光扫到旁边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巨大的抽象画。画框边缘似乎有点……新?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推了一下画框。“咔哒。”一声轻微的机括声。旁边一块墙板,
竟然无声地滑开了!露出一个嵌在墙里的保险柜!我心跳如擂鼓。这太顺利了!顺利得诡异!
我只是试试……保险柜是密码加指纹的。我肯定打不开。但就在我准备把墙板推回去时,
走廊尽头传来了极轻微的脚步声!有人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
慌忙躲进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后面。屏住呼吸。心跳声在死寂中震耳欲聋。
脚步声停在书房门口。然后是钥匙插入锁孔的轻微声响。门开了。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借着窗外微弱的路灯光,我看到了来人的侧脸。林雅琴!她脸上没有了白天的温和慈爱,
只有一片冰冷的焦灼。她快步走到那幅画前,熟练地推开画框,露出保险柜。
她输入了一串密码,然后把自己的大拇指按在指纹识别区。“滴。”保险柜门开了。
她迅速从里面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借着窗外微弱的光,她快速翻看着里面的文件,
表情凝重。她的手,在微微发抖。她看了一会儿,似乎松了口气,
又小心翼翼地把文件袋放了回去,关上保险柜门,推回墙板。她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目光扫过我藏身的窗帘。我死死捂住嘴,连呼吸都停止了。她似乎没发现异常,
快步离开了书房,轻轻带上门。我瘫软在窗帘后面,后背全是冷汗。她在找什么?
那份文件是什么?为什么偷偷摸摸?文仲渊的昏迷……真的只是意外吗?巨大的恐惧和疑云,
像冰冷的藤蔓,缠住了我。这一夜,我睁眼到天亮。第二天,周管家果然安排了司机。
一辆低调的黑色奔驰。“文**,夫人吩咐,带您去恒隆广场。”司机面无表情。
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师傅,麻烦不去商场了。”我开口。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去城西,锦绣家园。”那是我和我妈住了十几年的老小区。
车子停在破旧的小区门口,格格不入。我下了车,对司机说:“你回去吧,我自己转转。
”司机犹豫了一下,还是点点头,把车开走了。走进熟悉又狭窄的楼道,爬上五楼。
掏出钥匙,打开那扇斑驳的绿漆铁门。扑面而来的是灰尘和旧时光的味道。小小的两居室,
家具都蒙上了白布。一切都还保持着去年我妈走时的样子。我走到她的小卧室。
坐在她那张硬板床上。床头柜上,还放着一个廉价的塑料相框。
里面是我大学毕业时穿着学士服的单人照。她总说这张拍得最好看。我拿起相框,
手指拂过她每天都要擦拭的玻璃表面。灰尘。心口堵得难受。
视线扫过旁边那个掉了漆的五斗柜。最上面一层抽屉,半开着。我记得我妈走后,
我整理过她的东西,抽屉都关好了。谁来过?我拉开抽屉。
碎杂物:针线盒、老花镜(她舍不得买新的)、几本旧存折(上面余额加起来不到一万块)。
没什么异常。我下意识地伸手进去摸索。抽屉很深。指尖触到抽屉最里面靠背板的地方,
似乎……有点不平?我用力往里探。指腹摸到一小块微微凸起、用胶带粘着的东西!
我心脏猛地一跳。小心翼翼地把那东西抠了下来。是一张小小的、泛黄的旧照片。
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女人很漂亮,
气质温婉,眉眼间……竟和我有五六分相似!她穿着一条现在看来很复古的碎花裙子,
背景似乎是在一个公园。婴儿的脸看不真切。照片背面,
用娟秀的蓝色钢笔字写着:“晚晚百天留念。摄于滨江公园。1989.10.25。
”晚晚。我的名字。1989年10月25日。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份,深秋。我颤抖着手,
展开那张纸。纸很薄,有些地方字迹已经模糊。是我妈的笔迹!歪歪扭扭的,
还有错别字:“晚晚:妈不知道你啥时候能看到这个。要是看到了,妈可能已经不在了。
妈心里憋着件事,憋了大半辈子,对不起你。你不是妈捡的。是有人把你交给我的。
那年秋天,我在镇卫生院做清洁工。那天傍晚,天快黑了,一个男人抱着个娃,
慌慌张张跑进来。娃哭得都快没声了。那男人看着很凶,脸上还有疤。他一把抓住我,
把娃塞给我,还塞给我一卷钱和一封信。他说‘大姐,行行好,养大她!别问!别声张!
不然我们都得死!’说完他就跑了,跑得飞快。我吓坏了,抱着娃,又不敢喊。那娃就是你。
小脸冻得发青。我心一软,就偷偷把你抱回我租的小屋了。那卷钱不少,够我们活一阵子。
还有那封信,是封口的,写着‘请交予收养吾女之善人’。我偷偷拆开看了(妈对不起),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就是你手上这张。照片后面有日期。信里还说,
娃右肩胛骨下面有块叶子形的胎记。我看了,你有。一模一样。信里还说,娃叫‘晚晚’。
后面还写了几句话,我看不懂,像是诗:‘秋深露重晚来急,稚子无辜离故枝。
他年若得春风渡,莫忘寒鸦栖老时。’落款只有一个字:‘渊’。妈没文化,不懂啥意思。
但知道这娃来头不简单,肯定有麻烦。妈怕啊!怕那些人找回来,
怕他们连你带我都……所以我谁也不敢说,连夜带着你离开了老家,
跑到了这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城市。晚晚,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吃苦,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可妈是真疼你啊!你就是妈的命!要是哪天……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要去找你亲生爹妈,
妈不拦你。妈只求你,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要是……要是他们对你不好,你就回来,
妈的家永远是你的家。妈李秀芬绝笔”信纸被我的眼泪打湿了一片。“渊”。文仲渊。
那几句诗……“秋深露重晚来急”……秋晚。“稚子无辜离故枝”……被绑架带走。
“他年若得春风渡”……希望被好心人收养。
“莫忘寒鸦栖老时”……不要忘记在困境中栖身的老鸦(指养母)?我妈。她不是捡到我。
她是冒着天大的风险,藏起了我,保护了我一辈子!她识字不多,却牢牢记住那几句诗,
记了二十多年。她把照片和信藏得这么深,是怕给我招来灾祸,也是怕失去我。而我,
竟然真的找到了亲生父亲。可那个家……我把脸深深埋进信纸里,泣不成声。妈,
我该怎么办?浑浑噩噩地回到文家别墅。天已经黑了。刚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