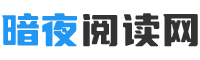专为书荒朋友们带来的《两次真心的光影》主要是描写秦浩戴婉芮晨之间一系列的故事,作者作者潘西来细致的描写让读者沉浸在小说人物的喜怒哀乐中。本书共计22633字,两次真心的光影第2章,更新日期为2025-11-15 16:52:00。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已完结。小说详情介绍:”她说,“它让技术有了温度。”那一刻,秦浩觉得,自己沉寂多年的某部分,正在苏醒。会后是自由交流。秦浩端着咖啡走到窗边,正翻看戴婉工作室的往期项目,她走了过来。“你刚才说的‘记忆地图’,能再详细说说吗?”她问。他抬头,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雪松香,像山间晨雾。“比如,”他放下咖啡,调出手机里的一张老照片,“...
《两次真心的光影》免费试读 两次真心的光影第2章
上海的秋天总是来得晚,却走得更慢。
十月的风已带凉意,梧桐叶在黄浦江畔打着旋儿,像一封封未寄出的信,飘向城市的缝隙。戴婉站在外滩美术馆的玻璃幕墙前,看着自己的倒影与对岸的灯火重叠,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误入他人梦境的过客。
她刚结束一场策展提案会。
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可她的后背还是渗出了薄汗。投影仪的光打在墙上,映出她精心准备的PPT——“城市褶皱:被遗忘的日常”。主题源于她去年在杨浦老城区拍摄的一组照片:晾衣绳交错的弄堂、锈迹斑斑的铁门、阳台上枯萎的绿植、老人坐在藤椅里看报的侧影。她想用这些被时代忽略的细节,拼出一座城市的呼吸。
“想法很动人。”主策展人陈砚推了推眼镜,语气平缓,“但不够‘爆点’。现在观众要看的是冲突、是流量、是话题性。你这组作品,太安静了。”
“可正是这种安静,才最接近真实。”她声音不大,却很坚定。
陈砚笑了笑:“真实不等于有效。我们不是在做田野调查,戴婉,我们在做展览。资本要回报,媒体要热度,观众要共鸣——你得让他们‘哇’出来。”
她沉默。
她知道他说得对,也知道他说得不对。
陈砚是业内公认的“点金手”,三十岁出头就策划过三场全国巡展,作品被《艺术新闻》称为“重塑城市美学的先锋”。他欣赏戴婉的敏锐,却总说她“太理想主义”。
“你有天赋,”他曾对她说,“但艺术不是一个人的独白,是群体的共谋。”
可那一刻,她只觉得心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像穿了不合脚的鞋,每走一步都疼。
戴婉不是没被人拒绝过。
大学时,她第一次策划校园艺术节,想做一场“无声对话”:邀请听障学生与健听学生共同创作装置艺术。她熬了三个通宵写方案,跑遍全校拉赞助,最终却被学生会以“执行难度大、受众面窄”为由否决。
那天晚上,她坐在美院天台,抱着膝盖哭了一场。
室友劝她:“算了,又不是什么大事。”
可对她来说,是大事。
因为她看见那些听障学生在排练时的眼神——专注、渴望、带着一点点小心翼翼的期待。而她,没能替他们把声音“看见”。
后来她独自在校园角落办了一场小型展览,没有开幕式,没有媒体,只有几盏灯、几幅画、几个愿意来的观众。
她记得一个戴助听器的女孩站在一幅画前,用手轻轻抚过画布的肌理,然后回头对她笑:“我‘听’到了。”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要走的路,注定不会太顺。
可她没想到,这一次的拒绝,来得如此彻底。
三天后,她收到正式通知:她的提案未被采纳。
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名为“赛博霓虹:未来都市幻想”的展览,主视觉是荧光粉与电子蓝的碰撞,主题是“科技与欲望的狂欢”。
她站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看着电脑屏幕上被退回的邮件,忽然笑了。
笑自己天真,笑自己执着,笑自己明明知道现实是什么,却还一次次撞上去。
她想起父亲的话。
他是个老派的中学语文教师,书架上摆满了鲁迅、沈从文、里尔克。她高考报艺术系时,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可以去追光,但别忘了,光是从裂缝里照进来的。”
她当时不懂。
现在懂了。
有些事,明知不可为。
可偏偏,就是想为。
那天夜里,她没回家。
她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城市褶皱——独立策展计划”。
她决定自己做。
没有经费,她就用自己的积蓄。
没有场地,她就联系老城区的社区文化中心。
没有宣传,她就一条条发小红书、豆瓣、公众号,甚至去弄堂里贴手绘海报。
她跑遍了杨浦、虹口、普陀的老街,拜访那些愿意让她拍照的居民。
有位独居的老太太,家里堆满了旧书和老照片,看见她来,颤巍巍地拿出一本泛黄的相册:“这是我老头子六十年代拍的,你要不要看看?”
她一页页翻,指尖触到那些斑驳的影像,忽然觉得,这些被遗忘的时光,比任何霓虹都更耀眼。
她请来学摄影的同学帮忙布光,请学设计的朋友做展签,请学编导的室友拍短片。
她甚至说服了那位听障女孩,用陶土创作了一组“声音的形状”——那些起伏的曲线,是城市车流、人语、风声的波形转化。
每一步都难。
有人笑她傻:“你图什么?又没奖金,又没职称。”
她只是笑笑:“图它存在过。”
展览开幕那天,下着小雨。
地点是社区活动室改造的临时展厅,空间不大,灯光也不专业,可来的人比她想象的多。
有附近居民,有艺术院校的学生,有偶然路过被海报吸引的年轻人。
她站在门口,看着人们在作品前驻足、低语、拍照,忽然眼眶一热。
一个中年男人在一幅照片前站了很久——那是他母亲生前住的老房子,去年已拆迁。
他转头对戴婉说:“谢谢你,让我再看她一眼。”
她点点头,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她收到一条陌生微信。
是陈砚发的,只有一张照片:他在展览入口处拍的,墙上写着一句话,是她写的前言:
“我们总在追逐光,却忘了影子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有些记忆,不必宏大,只需真实。”
下面一行字:“我错了。这组作品,值得被看见。”
她没回。
只是把那条消息,截了图,存进手机相册,命名为:“第一次真心”。
展览只持续了七天。
结束后,她把所有作品打包,送还给提供照片的居民。
有人问她:“还会再办吗?”
她说:“如果还有人愿意看,就会。”
她知道,这条路很难走。
资本不青睐,媒体不关注,大众可能转身就忘。
可她还是想走。
因为她终于明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莽撞,而是清醒后的选择。
是知道前路荆棘,却依然愿意把心交付。
是哪怕只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了”,也值得。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巨大的白墙前,墙上没有画,只有无数细小的光点,像星星,像雨滴,像城市里每一个平凡却真实的瞬间。
她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可以让它们被看见。”
她醒来,天还没亮。
打开电脑,收到一封邮件:北京一家创意工作室邀请她参与一个城市记忆主题的项目交流会。
她盯着发件人名单,看到一个名字:秦浩。
她不知道他是谁。
可她忽然觉得,这个名字,像一粒埋在土里的种子,正悄悄发芽。